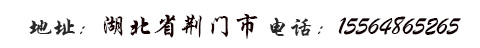玻璃城与语言游戏
|
北京治疗白癜风哪个医院专业 http://m.39.net/baidianfeng/index.html 01 奥斯特与《玻璃城》 (保罗·奥斯特其人) 保罗·奥斯特是美国当代小说家、诗人以及电影编剧。他在成名作《纽约三部曲》的第一部《玻璃城》中大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因为一次意外事故而失去了妻儿的侦探小说家奎因,由于一通打错的电话而受托保护彼得·斯蒂尔曼,一位说话有些语无伦次却声称将要被出狱的父亲所杀死的年轻男子。虽然奎因常常以其作品主人公马克斯·沃克的身份在想象空间内经历种种冒险,但在现实中扮演侦探的角色却是从未经历过的事情。为了追踪老斯蒂尔曼的踪迹,他去图书馆查阅了这位前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教授的著作,并了解了他曾经在儿子身上所从事的恐怖实验:小斯蒂尔曼曾经整整九年被父亲关在一个门窗封闭的黑暗小屋内,同其他人类没有任何接触,为的是一个疯狂的目标——彻底遗忘人们日常使用的语言,而学会某种人类真正的“天生的语言”。 在一丝不苟地跟踪出狱的老斯蒂尔曼的过程中,奎因发现这位穿着邋遢的白发老人似乎只是在曼哈顿几个有限的街区内漫无目的地散步,时不时停下来收集一些被人遗弃的废物,这些可疑的行迹都被他记录在一本红色笔记本上。之后一次有意策划的会面中,奎因从老斯蒂尔曼的口中再一次确证了他那根植于神学的神秘使命:收集这个混乱世界中的破碎残骸,并给它们命名以发明一种新的语言。 (于曼哈顿跟踪老斯蒂尔曼的奎因)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跟随老斯蒂尔曼在纽约这座现代迷宫中打转时,一些细微的变化也开始在奎因身上发生:饮食与睡眠的需求迫于监视的任务而衰退,甚至对于时间的感知也在消逝。他藏身于斯蒂尔曼家前门的一个偏僻的小巷中,巧妙地躲过了他人的注意。在等待目标露面的无聊时间内,他只能将目光投向在缝隙间呈现的天空: “一次又一次,所有的天气现象都从他头顶上飘过了,从阳光灿烂到狂风暴雨,从沉沉阴霾到晴空万里。还有黎明和黄昏,正午的变换,迟暮和深夜。即使是在漆黑一片的夜里,天空也没有休息。云层从漆黑的夜空飘过,月亮永远以不同的形状出现,风继续在吹。有时候甚至会有一颗星星缀在奎因头上那一方天空,当他抬头时,他会想它还在那里吗,还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烧尽了。”(《玻璃城》)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很久,直到奎因的钱花光了,并从最初那通电话所要找的侦探奥斯特(作者的文字游戏)口中得知老斯蒂尔曼已于两个月前跳桥自杀。故事以奎因进入老斯蒂尔曼藏身的公寓而结尾。在四壁空空的房间内,早已记不清自己是谁的奎因不分昼夜地在他的红色笔记本上书写,像老斯蒂尔曼给万物命名那样写着世界里的一切。最终,故事的情节随着他的失踪戛然而止,而进入公寓的侦探奥斯特在屋内找到的仅仅是摊在地板上的那个小本子。 02 巴别塔 《玻璃城》借侦探小说的架构起始,却又以荒诞的转折与结局将其彻底击碎。无论奥斯特本人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后现代文本常常具有的断裂与去中心化特征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明确意义虽然被消解了,小说却又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从小斯蒂尔曼的实验,到老斯蒂尔曼的神学著作,再到奎因所经历的那种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转变,一条重要的线索逐渐浮出水面:正是福柯曾敏锐捕捉到的那种词与物的断裂,以及弥合这种断裂的尝试。后者在书中正是以著名的“巴别塔”隐喻的形式登场。 (巴别塔) 对于奎因来说,扮演着“通向另外一个地方的桥梁”之角色的正是在图书馆查阅的那部老斯蒂尔曼的著作《伊甸园与巴别塔:新大陆的早期意象》。在书的第二部分中,老斯蒂尔曼描绘了狂热的清教徒亨利·达克(作者奥斯特杜撰的人物)的生平。根据老斯蒂尔曼的考证,出生于英国,后来远渡新大陆的达克曾经写出了一本弥尔顿《复乐园》式的大胆作品《新巴别塔》。这部作品的结论正与老斯蒂尔曼后来的使命一致:通过扭转语言的堕落,人们可以重现伊甸园里的语言。达克预言:在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港的三四百年以后,英国移民们将会完成这一神圣使命的第一部分工作。届时,新巴别塔的地基将会在大洋彼岸的新大陆初步搭建完成。 (五月花号移民船) 那么,亨利·达克所指的三四百年后究竟是何时呢?按照奎因的推算,正是年前后。在小说中,这是老斯蒂尔曼将他的儿子关起来的时候;而在现实中,这是奥斯特本人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比较文学的时期,也正是德里达写作《书写与差异》以及福柯写作《词与物》的时代,是后结构主义向结构主义发起挑战以及解构思潮应运而生的岁月。 在70年代旅居巴黎期间,奥斯特曾受《纽约时报》编辑的委托翻译了当时福柯与萨特等人发表的许多专栏文章。从某种程度上说,《玻璃城》中关于塞万提斯的段落呼应了福柯在《词与物》的第三章“表象”中所进行的哲学讨论。作为为数不多的从哲学层面赋予堂吉诃德这一文学形象以重要意义的哲学家,福柯如是评价道: “《堂吉诃德》勾勒了对文艺复兴世界的否定;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相似性与符号解除了它们先前的协定;相似性已靠不住了,变成了幻想或妄想;物仍然牢固地处于自己的嘲笑人的同一性中: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它任何东西;词独自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是物的标记;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中。”(《词与物》) 而在奥斯特借奎因之口所作的大胆评价中,堂吉诃德这一形象以反讽揭示了这种断裂: “在我看来,堂吉诃德是在做一个实验。他想试一下他伙伴们会不会轻易上当受骗。他在想,有没有可能站在世界面前,以绝对坚信不移的口吻漫天撒谎大放厥词?把风车说成是骑士,把理发师的脸盆当作头盔,把木偶视为真人?有没有可能让不相信他的人也认同他的说法?换句话说,如果他能给人们带来乐子的话,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他的渎神行为?”(《玻璃城》) (堂吉诃德与风车搏斗) 当现实中找不到书中记载的巨人时,人们又该如何成为英雄呢?堂吉诃德同风车搏斗的荒诞行为源于他对于那种大写的“律法”(laLoi)的服从,源于证明中世纪骑士小说中种种符号(城堡、夫人、军队等等)背后的真实世界的尝试,然而却使他自此成为了疯人的典型。风车和巨人之间,除了体积巨大这一特征外存在着诸多差异,但那种古典的相似性诡计却诱使堂吉诃德名正言顺地将其视为一物(或许在骑士小说著成的那些年代,风车与巨人就是某种一致的东西,正如人们还将人体器官与地质要素等同起来)。自17世纪的科学蓬勃发展以来,这种魔法一般的把戏便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成为了妄想与癫狂。塞万提斯则正是那个划时代的、向人们展示这种不合时宜的疯癫性的作家。 这事实上表明了某种福柯所说的“知识型”的历史转折: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能指、所指与“关连”透明地叠加在一起且被归结为单一形式的情况一去不复返了。换句话说,从人们意识到能指(例如作为符号的“红色”二字)与所指(“红色”所指向的具体事物)相对应的二元结构及其衍生的问题时起,语言的堕落便是不可逆转的。语言变成了存在的缺席,符号也不再内在于事物本身。词与物的割裂造成了康德的“物自体”式的不可知论难题。语言想要把握事物,却始终与其处于一种表象关系中;而事物本身则讽刺地“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 这些老斯蒂尔曼将之视为衰败的迹象被细致地记录在了他的著作中。而在后来与奎因的对话中,他也举例说明了这种语言的堕落:当人们说到“雨伞”一词时,脑子里浮现的无非是某种由金属杆与帆布构成的,用来挡雨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词语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承担了人们赋予一件物品以某种功能的意志。老斯蒂尔曼于是请奎因设想一种情况:一把只有伞骨,无法用来挡雨的伞——在去除了功能之后,人们还能够用同样的词语表达事物吗?在前者看来,某些退而求其次的说法(例如“雨伞坏了”)是危险的,因为这种策略自然而然地掩盖了本来应该被直接说出的东西(那个无法用来挡雨的奇怪东西究竟是什么)。事物的原貌在理性分类学的暴力中被遮蔽了。 (”雨伞“或其它?) 与之相对,巴别塔是伊甸园式的理想状态的复归:人们在某种天真无邪的状态下,舌头能够再一次地直指世界的内核。他的词语不仅揭示事物的本质,还真正地赋予他们生命。总而言之,那便是要使语言所构造的理性世界(依赖于真理的宣扬与表达,仅仅在可被言说处享有某种孤独主权的世界)与真正的、原貌的世界再次合二为一。 老斯蒂尔曼的确在小彼得身上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彼得现在可以像别人那样说话了。但是他脑子里还有别的词句。那是上帝的语言,别人都不能说。它们无法被翻译。这就是彼得为什么能活得离上帝那么近。这就是他为什么成为了一个有名的诗人。” 03 能指游戏 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巴别塔这一语言的乌托邦被搁置了起来。小斯蒂尔曼被警方从解救出来,而一切的始作俑者老斯蒂尔曼则锒铛入狱。在出狱后的那段有限时间里,重构巴别塔的努力仅仅停留在一些粗浅的尝试。与老斯蒂尔曼有关的一切线索随着其跳桥自杀的消息而中断,而他的使命则隐蔽地转移至奎因身上继续下去。以某种隐喻的形式,在后者身上发生的转变显示出了故事的意义: “现在这案子已经被他远远地扔在脑后,他早就不再费心想这件事了。那曾是他生命中通往另外一个地方的桥梁,但现在他已经过来了。桥的意义也就不再存在了。奎因对自己也越来越不在意。他写星辰,写地球,写他对人类的希望。他感到自己的语言已经切断了与自己的联系,现在它们已经成了大千世界的一部分,真实而具体,就像一块石头、一片湖,或是一朵花。 它们不再跟他有任何关系了。他想起自己出生的那一瞬间,以及他是如何从母亲子宫里被轻轻地娩出的。他想起这世界和所有那些他曾爱过的人的无限善意。除了所有这一切的美好,什么都不重要。他想把这种感触接着写下去,但令人痛苦的是他知道这不可能。尽管如此,他还是试着鼓起勇气来面对这个红色笔记本的尽头。”(《玻璃城》) 将红色笔记本写完,即是要把命名世界的游戏推向极致,从而达成某种奇迹般的逆转。如果人们想要超越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命名暴力,反而需要以讽喻的方式将语言符号的荒诞游戏进行下去,从而打破那些静态的、僵死的、充满局限却又缺乏反思的指称关系,创造出对真理与意义的一元构建之外的其它可能。 在德里达看来,后现代时期的语言中甚至连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关系都难以为继,而仅仅剩下能指的无限游戏。语言的生命力来自于无尽的变形与生成,来自于不断的自我分裂与破除界限的生产性过程,来自于捕捉到词与词之间的细微差异并发掘出断裂的时刻,而并不是来自于对先验在场的所指的追寻,即在巴别塔的隐喻中被重新找回的那些本质上属于上帝的符号对应物。 (他写星辰,写地球,写他对人类的希望......) 而小说结尾处老斯蒂尔曼与奎因的双双失踪,也恰恰象征着这种追寻的结束与一种新的运动的开始。当书写的绝对优先性被确立之时,人也便会像福柯所说的那样最终“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而被抹去”。奥斯特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所作的预言是明确的:那种自认为能够把握一切意义与线索的主体性,终将为文字那无尽的沉默运动所湮没。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ulimaosi.com/plmsdt/10450.html
- 上一篇文章: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管教育山东校友中心
- 下一篇文章: 不做观光客,玩儿就玩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