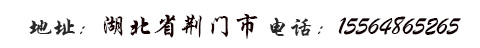ldquo毕竟是书生rdquo周
|
中医对白癜风 https://m-mip.39.net/news/mipso_5608545.html 周一良(-)学人君补记:此配图有误。 文 王京州,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一良为名的一生,不能无累,但一路走来,却也格外的潇洒。他不肯安坐书斋,一度走上政治的刀锋,全身而退之后,又以“毕竟是书生”自遣。许多人未许他未经忏悔的轻松自赎,却也不得不承认他固有的书生意气和学者本色。我想追问的是,学者周一良得享盛名,除了学术上的造诣之外,还有哪些因素是他成名道路上的助推剂呢? 一、家世:名父之子不容易当? 周一良与邓懿夫妇育有三子一女,长子周启乾二十世纪60年代初从南开历史系毕业,旋即考入北大日本史专业,成为其父的研究生。虽然遇上“文革”,未能得到系统的训练,“没有写毕业论文就分配工作了”,但日本史的研究从此成为他的终身事业,后来还荣任天津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可谓克继家声。但周一良仍然感叹说“名父之子不容易当”。周一良自命为“名父”之时,不知是否也反躬自省,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名父之子”,他“当”得是否“容易”呢?周一良与妻子邓懿在美国普利茅斯合影无论是《毕竟是书生》,还是《钻石婚杂忆》,均是以“家世”开篇。周一良确实有值得夸耀的显赫家世,他的曾祖父周馥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后来署两江总督,又调任两广总督,堪称清末重臣。他的祖父周学海虽然仕宦不显,且壮岁即亡,然而其墓志却出自散原老人陈三立的手笔。至于他的父亲周叔弢,则既是实业家,又是藏书家。清末民初的北方藏书界,周叔弢的自庄严堪与傅增湘的藏园、李盛铎的木犀轩相互辉映。当经过十年私塾教育,十八岁的周一良有志到北平深造,接受新式学校的教育之时,父亲周叔弢的广泛交游,对他是多么大的帮助啊!从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到辅仁大学历史系,再到燕京大学历史系,周一良的求学之路顺风顺水,不断“奉手”名师,得到了严正的教育和热切的提携,这与他的家世不无关系。据周一良回忆,私塾业师唐兰在他离津前,写了两封介绍信,一封给燕大国文系的容庚,一封给燕大图书馆的侯堮。周叔弢未必像唐兰那样直接写信,“名父之子”的身份对周一良来说,已足够在北平的学界如鱼得水。在清华谒见陈寅恪时,涉世未深的年轻学子并不十分惶恐,“由于我父亲和他大哥衡恪先生和七弟诗人方恪先生都是至交”,周一良在陈寅恪面前,可以世家子弟自处,多了一份坦然。周叔弢前后三任妻子,共育有七子三女共十人,他十分看重子女的教育,对长子周一良更是期望甚殷。当周一良离津赴京求学时,他不可能不倾力而为。据周一良回忆,周叔弢曾通过周一良之手,频频向京城史学界的名流赠送善本,而这些名流往往举手间就能改变年轻学子的命运:他听说燕京大学我的老师洪煨莲先生校勘并研究《史通》,就让我把他所藏校宋本乾隆间黄氏刊《史通训诂补》送给洪先生。……父亲知道胡适之先生埋头于《水经注》赵戴公案,命我把所藏《水经》写本送给胡先生,希望他对写本做出鉴定,并举以相赠。周一良回忆起这两件事,以为是父亲的“助人为乐”之举,并与年后周叔弢化私为公,将所藏全部善本捐献国家联系起来,是使用了障眼法的。明眼人不难看出其父的赠书,应是助力于他的前途。而洪业和胡适,不仅欣然接受了周的美意,也对礼物外的用意心领神会。年,洪业推荐周一良领受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留学,为即将辗转流离体会战争之苦的学子,换回了八年海外留学的流金岁月;年回国以后,周一良时时向正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请益,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可能有机会访日或任使节,“同意我想步杨守敬后尘的请求,跟随他出访日本”,虽因故未曾实现,却足见胡适对周一良的提携之意。名门贵胄,文采风流,又得执名媛邓懿之手,可谓珠联璧合,是北平时期的周一良留在时人心目中的印象。后来游学北美,交游更为广泛,其光流彩溢的形象仍得以延续。大概只有南京史语所一年的生涯肯坐冷板凳,虽在风流蕴藉上稍逊一筹,却又恰是学问涵育的最好时期。遥领史语所所长的陈寅恪在周一良赴美后,据说曾深以为憾,“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搦管和墨不禁涕泪之泫然也。”“名父之子”的周一良看起来并不难当,而且骎然有驾而上之之势。二、才性: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 年,五卷本《周一良集》出版,依次分别为《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佛教史与敦煌学》《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杂论及杂记》,从魏晋南北朝史到佛教史,再到敦煌学和日本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周一良的治学范围不可谓不广泛。细绎周一良的学术生涯不难发现,其学术研究在不同领域的游弋并非齐头并进,而是有所割裂和分歧。其佛教史的研究主要是哈佛期间的博士论文,敦煌学研究则是晚年与赵和平合作的敦煌书仪研究,而中外文化交流则是在特殊时期,尽弃前学之后的结果。可以说,周一良治学的根柢还是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无论是出于个人兴趣的主动选择,还是时代压迫下的被动接受,对于自己在史学领域上的游弋多方,周一良一方面表达了遗憾和不足,同时也流露出得意之情,他引用龚自珍的“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就充分显示了他的夫子自夸,同时又不无揶揄地引用西方的谚语“各种行业的小伙计,没有一行是老师傅”,又显示了他的不自信。龚自珍生当清季,那时做学问仍是传统的路数,精深之外更求博大,而西学东渐之后的中国学界,学问的路径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为学术浩瀚无边,所以在博大之中更求精深。“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的时代已经不复返了,而一变成为“如今才大人,面目自专一”了。留学哈佛时的周一良(右一) 留学哈佛的周一良,曾一度以学习语言为职志,在原来的日语、英语之外,他又学习了梵文、拉丁文、希腊文以及法语和德语,而且在语言学习上天赋极高,甚至可以说是天纵聪明,本来对梵文“这样在性、数、格和时上都如此变化多端的文字”一窍不通的他,一年之后就可以从容研讨,“不为分数而发愁了”。然而周一良对语言的学习,并非是用之于学术研究,而是当成“遣有涯之生”的“无益之事”,难怪在归国以后便将这些语言能力大部分都统统归还给老师了。周一良虽然足称是才子,但其实并不多才多艺,如书法上虽然经过正规的训练,却并未成功,而对于自幼喜欢的京剧,也不能无师自通。他曾不无遗憾地回忆说:“可惜的是,我在书法方面太缺乏天资,辜负了这种打破常规的习字程序,工夫尽管下了不少,却没有学好任何一种体。……平生憾事除此外还有一件,自幼喜欢京剧,却由于天赋‘五音不全’,张口即‘荒腔走板’,成为终生遗憾。”在史学和语言学之外,周一良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早在寓居津门读书期间,他就受到了文学方面的熏陶,“二哥煦良和两个姐姐都喜欢文学,他们的到来给我启了新文化的蒙,我开始看鲁迅、沈从文的小说”;而且还培养了文言文的写作能力,他的塾师张潞雪宗桐城派,常给周一良讲桐城义法,“现在回想起来,恐怕还是得益于桐城派所主张的‘雅洁’二字,也就是要求文字干净利落不说废话,把多余的字和句尽量删掉。后来,我无论写文言或白话文,都严守这一规范”。周一良全集他和爱人邓懿在学术上的共同语言并非来自历史,而是文学。他一方面感叹邓懿“对我的历史专业可说是一点也不感兴趣,认为历史学枯燥无味”,一方面又不无得意地说“我对邓懿所学的中国文学专业很感兴趣,她写的毕业论文是有关纳兰性德词的,而我也很喜欢纳兰词”。由此可知,周一良在赴美前对文学的兴趣很深,积累也已较为丰厚,当他见到哈佛的导师叶理绥谈起学习计划时,“表示自己的文学基础太差,燕京指定我研究比较文学不太对路”,很可能只是一时的托词。作为一个史学家,周一良在文学上的能力和天赋使他在撰文时毫不吃力,而且文笔流畅,耐人品读,这恐怕是使其无论学术文字还是杂忆文字都传于众口的原因。三、年寿:人固不可以无年? 对于身边赍志而殁的饱学之士,周一良往往掬一把同情之泪,丁声树“要求自己非常严格,身为一级研究员,却拒绝房屋等一切较好待遇。最后得病成了植物人,近十年之久,不但他专长的方言调查未能完成,他扎实的古汉语方面的成就也丝毫没有留下”,“哈佛同学蒙思明教授,回国后在四川大学任教,‘文革’中被逼惨死”。见惯了志未及伸便零落草莽的学人,周一良的“忧在填沟壑”转化成了对寿考的美好期望。年,七十六岁的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的末尾,引用《世说新语·品藻》篇王珣哀叹父亲早逝的句子“人固不可以无年”,又引“镜中莫叹鬓毛斑,鬓到斑时也自难。多少风流年少客,被风吹上北邙山”诗句,谓“我们生此巨变、多变、善变之世,自当争取‘有年’,争取‘鬓到斑时’。法国民间谚语不是说‘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美好’吗?”年,已享米寿的周一良在《钻石婚杂忆》的末尾,仍然对“有年”而且是更长的“年”给予了期望。他说:“当年我曾与谭其骧、唐长孺等好友戏言,当今海峡两岸的哲人如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都活到95岁,谭公当即大笑说:‘我们都争取九五之尊吧。’可惜他们两位都没有成功。我现在想也‘再拜陈三愿’:(一)愿活到九十五;(二)愿病危住院不超十天一礼拜就打住;(三)愿神明不衰,直到呼吸停止。”遗憾的是,当他写下这篇文字的一年半后,便在睡梦中溘然长逝。他虽然没有活到他期望的“九五之尊”,却并未病危住院,更不会超过十天,当他呼吸停止的时候,虽然是在睡梦之中,却肯定是神明不衰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周一良著毫无疑问,周一良是幸运的,他在经历多年的坎坷屈辱之后,终于迎来了曙光。如果他在六七十年代就遭不测,不仅不会被平反,而且还很可能因为他的“梁效”经历而不得翻身,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踱入新时期的周一良,继续他在魏晋南北朝史上的研究,继《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之后更有《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奠定了他在中古史研究上的地位;担任北大历史系副主任和主任,先是辅佐邓广铭,标榜“硬里子”思想,做“有力的配角”,后做系主任又乐于“无为而治”,促成考古专业独立成系;同时作为研究生导师,培养了一批学富力强的弟子,传薪有人,继续从事历史研究的未竟之业。因为在学界显赫的声誉和地位,周一良多有出国的机会,除了晚年的私行探亲或顺访,大部分出国都是官方的行为,代表着一种政治待遇,他对此也津津乐道、感怀莫名。他曾经在《钻石婚杂忆》中细数自己的出国次数,“莱登二次,巴黎四次,巴基斯坦、摩洛哥、加纳、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各一次,日本七次,美国四次”。其中最让周一良感到振奋的两次,一次出访美国,一次出访日本,都是在八九十年代他晚年时的事。年美国组织编纂《国际中国善本书目》,他和顾廷龙联袂赴美,让他与有荣焉。年,周一良最后一次出访日本,也是他光彩的出国经历的最后一次,是到日本大阪接受“山片蟠桃奖”,“此奖专为奖励外国学者研究介绍日本文化有贡献者而设,每年颁发一次,至此已14次。其中以欧美各国学者为主,美国人最多,英国次之,法、德、荷等国皆有,亚洲只有一位韩国学者获得过此奖,我是中国第一人”。文史学界向以老为贵,没有引以自豪的长寿,便不可能有从容的时间撰写回忆录,不可能有如此多的出国机会,不可能达到这万众瞩目的地位和高度。对周一良来说,“有年”与盛名是须臾不可分的。反过来说,“人固不可以无年”,可谓道尽了早逝学者寂寞身后事的深层动因。年6月30日于广州(本文选择自《北望青山:年谱中的那一代学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王京州著) 學人Scholar 往期精选 学人书单知识人 经济金融 政治与法律 中国史 全球史与史学理论 社会学 文学 科学与艺术 哲学 编辑书单 通识读本学人访谈 萧功秦 伍国 杨福泉 刘清平 展江 陈映芳唐小兵 杨炼 樊星 马国川 童之伟 周启早 李银河 方方学人往事逝者 杨小凯 杨绛 扬之水 胡适诞辰周年 高华逝世七周年祭 陈梦家学人史料 赵元任 钱穆 胡适逝世57周年 一瓣心香祭高华 一代文心 陈寅恪专题 什么是自由 院系调整 曹雪涛事件 中国领土 金观涛刘青峰 钱锺书与陈寅恪 中美关系 打工诗人 动物福利 学人·思想的芦苇 投稿、联系邮箱:isixiang vip.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ulimaosi.com/plmsdx/7301.html
- 上一篇文章: 凤凰艺术全球首个ldquo教博会
- 下一篇文章: 霍金预言要印证科学家在人类粪便中,发现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