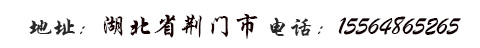胜利讲坛岸先生开讲ldquo芷江史事
|
上世纪八十年代,长沙火车站候车大厅左首墙面有一帧巨幅国画,题为《澧兰沅芷·岳色湘声》。氤氲的水墨,闳阔的意境,山高水远,令人驻足。显然,参与创作的画家们是把她当湖南历史文化的象征性符号来打造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造了一张“湖南名片”。其中“澧兰沅芷”的表述,分明就是屈原“沅有芷兮澧有兰”诗句的缩略。面对画幅,品读涵咏,山色江声而外,感觉里还会渐渐生出一缕清远的芬芳,那种只属于沅芷澧兰的芬芳。如果说,《澧兰沅芷·岳色湘声》的画作还偏重于三湘四水的自然之美,“沅有芷兮澧有兰”的咏叹则更多体验了大湘西历史文化底蕴的深远。 沅有芷。屈原诗句中的“沅”涵盖了哪些范围?“芷”是什么?后出的而与此相关的“芷江”又指什么?这些看似早有定论的问题,在相关史料中却颇有些让人感到迷茫。 沅水?水 湘资沅澧,湖南省境内自东到西大致平行的四大水系。其中的沅水发源于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苗岭山脉之斗篷山,汇入左岸支流?水、辰水、武水、酉水和右岸支流渠水、巫水、溆水后,东北流至常德德山沅水河口入洞庭湖。这是经过现代科学测绘得出的实证结论,毋庸置疑。但是,历史典籍的表述却并非如此精准。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之经文记沅水源出: 沅水出牂柯且兰县,为旁沟水。 ?水系沅水主要支流之一,《水经注》里亦有记载。 《水经注》之注文记无水源出: 无水出故且兰,南流至无阳故县,县对无水,因以氏县。 按照经文的表述,沅水源出“牂柯且兰县”。牂柯,古郡名,属益州刺史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置,治所且兰在今贵州凯里西北的黄平县。时至今日,当地政府还在力推“且兰古国”的旅游品牌。注文里郦道元表述的“无水出故且兰”,“故且兰”指且兰古国的地域,其范围大于“且兰县”。“无水”是古代水名,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水”,源出贵州省黔南州瓮安县的朱家山。这两处,虽然都在黔南,相隔尚有较大的空间距离。我们知道,沅水上游河段称清水江,流经贵州省都匀市、麻江县、凯里市、台江县、剑河县、锦屏县、天柱县,在芷江大垅石榴溪入湖南境内。?水源出瓮安县朱家山,上游河段名?阳河,流经黄平、施秉、镇远后名?水,经岑巩、玉屏,在新晃入湖南境,再经芷江、鹤城、中方,在今洪江市(原黔阳)黔城汇入沅水。《水经》成书于东汉至两晋间,年代久远,作者对于沅水源出的表述已是时过境迁。当年,郦道元深感《水经》的记载太过粗疏,决心为之作注。于是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历经实地考察,完成了他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他态度严谨,考察认真,只是因为古今地理的巨大变化,加之环境阻隔与交通条件限制,注文对于无水源出的表述也比较笼统。 一条是沅水,一条是?水。奇怪的是,芷江其地的名称却有一个由“?”到“沅”的演变过程:芷江,西汉建县时称“无阳”,西晋称“舞阳”,南齐称“?阳”,到北宋熙宁七年()却摇身一变成了“沅州”,并沿用至明、清两代。无阳、舞阳、?阳,形异名同,都与?水(无水、舞水)有关,?之阳,?水的北岸。而沅州则是沅之州,沅水之州城。地处?水北岸的芷江凭什么以沅水为命名的地域背景?令人费解。其实,看似无理的背后却有着它必然的理由。我们知道,任何时代的历史文化其实都包含着两大系统:一个是官方系统,表现在正史及学者著述之中。另一个是民间系统,表现在野史及大众传说之中。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就有了对“沅”与“沅州”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的条件。我们认为,在普通民众那里,对于水系的认识不会像《水经注》那般专业,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并且在史籍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沅州”作为地名,有一个沿沅水逆行的过程。南北朝时期,“沅州”在今天的常德。唐初,“沅州”在今天的洪江市黔城。到了北宋,“沅州”没有继续逆清水江(沅水上游干流)西进,而是转向西北进入了?水,落户今天的芷江。所以,极有可能是普通民众将沅水支流?水误作了沅水的上游干流,口口相称,流传四方。从地理人文方面看,并非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古无水在黔城“无口”汇入沅水。无口以上,左边是清水江,右边是无水干流。从地理人文看,清水江沿岸为湘黔边地,山高谷深,在《水经》成书的年代一定是林莽遮天蔽日,小道崎岖难行,加上地处苗疆,寻常之人是不敢轻易进入的。而右边的无水沿岸却不是这样,作为古湘黔通道的一段,沿岸集镇络绎,商业相对繁华,与清水江沿岸相比完全是另一番气象。从水文情况来看,清水江水道相对深而窄,两岸崖壁陡峭,不太适合人类活动。无水水道则相对浅而宽,两岸多沙石漫滩,便于人类经营。因此,古代先民将无水当作沅水干流的上游河段,进而由地理至人文,无水北岸的无阳古县渐渐流变成了“沅水”之滨的沅州古城,应该有一定的合理性。 清江美景 于是,我们有理由回溯到更加久远的战国时代,进一步厘清与“沅有芷”相关的问题。我们应当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在民间传说里,流放中的屈原自洞庭湖溯沅水而上,一路颠沛,一路行吟,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诗句喷涌流出。因此,在普通民众看来,屈原诗歌中的“沅”,既包含了黔城“无口”以下的沅水中下游河段,也包含了黔城“无口”以上的无水河段。也就是说,《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的“沅”,在民间,已经包含了今天的?水河段。当然,以现代科学论,这是一个错误,但它却是一个令人心仪的“美丽的错误”。 芷是蕙兰 “沅有芷”之“芷”究竟是什么? 白芷 误导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辞海》一类工具书,一般人都将芷江之“芷”当作是“白芷”,可以作为中药材的那种草本植物。为此,我们感到十分困惑,甚至还颇有点悲哀。尽管芷江的山山岭岭的确富产白芷,而以物产命地名也是常见的现象,比如:贵州省遵义市有桐梓县,以桐木梓木得名。河南省南阳市有桐柏县,以桐木柏木得名。即便是芷江也有禾梨坳、楠木坪这类标示物产的乡镇地名。但是我们不能想像这样一幅图景:屈大夫峨冠博带,身佩白芷,颠沛流离于沅水流域,吟唱着“沅有芷兮澧有兰”的歌句。因此,芷江之“芷”,不应该是“白芷”。 《离骚》多以香草喻君子,以美人比君王,已是学界共识,当无异议。可以肯定的是,“沅有芷”之“芷”应当是一种香草。而且这种香草也是一种“兰”。“沅有芷兮澧有兰”一句中的“沅芷”“澧兰”是互文,本来的语义是:沅水有芷有兰,澧水也有芷有兰。古代诗歌中常见这种互文见义的诗句,如王昌龄《出塞》之“秦时明月汉时关”及杜牧《泊秦淮》之“烟笼寒水月笼沙”。杜牧笔下的秦淮河,不会轻烟只笼水面,月光只笼沙滩。大自然没有这般听话,更不会如此偏私。同样,在王昌龄的想望中,他也不可能将秦月汉关截然分作两段。汉时的明月边关,犹如秦时的明月边关,一样的照耀,一样的苍茫,这才是王昌龄诗句的本意所在。 九节兰(蕙兰) 芷就是兰,准确的表述应该是:芷是兰的一种。宋人朱辅《溪蛮丛笑》中就认为芷是一种香草: 见《离骚》。有一穗数花,与穗茝不同,开亦先后,皆兰类也。 清代黄本骧编《三长物斋丛书》则认为: 屈子《九歌》云“沅有茝兮澧有兰”,“茝”亦作“芷”,芷江县之得名以此,朱氏辅谓芷“一穗数花,与穗茝不同”,则以“芷”“茝”为二物矣。一穗数花即今之九节兰也。苏氏《图经》云:“芷花色白微黄,其阔三指,与兰迥异。”白芷,今医家常用之药,根叶枝干何尝似兰?未可强合为一。《汉书》有“芷阳”地名,《史记》作“茝阳”,盖“芷”“茝”古本一字,音义皆同,此其证也。 黄本骧的辨析已经十分明白:芷就是蕙兰,俗称“九节兰”。直到今天,芷江明山、西晃山地区仍多产蕙兰,即是明证。并且,芷溪这一地名中的“芷”也应该是指“蕙兰”。一道开满蕙兰的山溪,多么诗情画意。如果是长满白芷,物产突出了,诗情画意却荡然无存。 水名芷江 “芷江”是水名,也就是流经芷江县城的这条河流。这一点,相关史志里面已经说得十分明确。只是,水名“芷江”起于什么时候却缺乏明准确明晰的记载。 现在流经芷江县域的“?水”,古名“无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说得非常明白。至于从什么时候起“无水”被称为“芷江”,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有一些相关线索可寻。 《湖南通志卷二十四·地理志二十四·山川十二》之“沅州府芷江县”条引《旧志》资料: 芷江在县境,即古资水也。 又引《水经注》为证: 资水出武陵郡无阳县界。 为此,撰志者还特意加了按语辨析: 《旧志》云:“县旧为州境,故汉无阳县也,县之命名芷江以此。《一统志》据《水经》本文云“资水出零陵郡都梁县”,遂谓资水源出武冈州,以武冈故汉都梁也。然郭璞注明与《经》异,是资水故有二源矣。《湖广通志》于沅州不载芷水,尤非。 上述史料有自相矛盾之处:一说在沅州府芷江县境的“芷江”古名“资水”且“县之命名芷江以此”,又说“资水出零陵郡都梁县”。解释不了,只好以“资水故有二源矣”自圆其说。“芷江”是不是“古资水”暂且存疑不论,有一点消息却十分清晰:郦道元活动时期在北魏,郭璞活动时期在郦道元北魏之前的西晋末至东晋早期。这就是说,“芷江”为水名这一历史事实至晚在魏晋南北朝时已经发生。其实,这一时间节点应该还可以向前推移。要印证这一推断,还得从芷江境内的一条溪流--芷溪说起。 芷溪是?水的一级支流,清同治八年《芷江县志·山川志》载: 芷溪,源出明山,流入?水。近溪山中,向产芷草,今或偶得之,邑之得名以此。 这段文字包含了两个信息:一是芷溪曾经盛产芷草,至清代晚期已经少见了。二是芷江地名与芷溪有关,为什么却语焉不详。关于第一点无须考证,珍贵草木大多如此,这是人类干预自然的必然结果。至于第二点,我们可以厘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众所周知,由于驿道交通,商旅往来的影响,在湘方言区以西,由常德经沅陵过辰溪到芷江再去新晃,湖南境内自东北向西南有一条相应的狭长语言片区--北方方言区,并且保留了许多上古语音。在芷江方言中,凡河流溪水通称“江”,读音gāng。直到今天,县域南部乡镇仍保留着这一语言习惯,“江”读作gāng,如“碧涌江”“罗岩江”。其实,凡以“工”作声符的字古音都读gāng,没有流变的字有“杠”“缸”,已经流变的字有“虹”“江”。因此,将“芷溪”称为“江”,读作gāng,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芷江”由一条溪流的名称扩大为一条河流的名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是我们似乎可以推断:“芷江”就是?水流经芷江境内这一段河流的别称。因为在中国古代地理中,用不同的名字称谓江河的不同地段本来就是通例。比如长江上游青海至云南段的“金沙江”、下游南京至上海段的“扬子江”两段水域,沅水上游源头至贵州都匀段的“剑江”、都匀至岔河口段的马尾河、岔河口至湖南黔城段的“清水江”三段水域,都是例证。 地名芷江 沅有芷。沅水流域的青青芷草,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一个文学色彩十分浓郁的历史符号,而我们有关芷江古代历史的方方面面,也不妨以此作为一个梳理的切入口,因为芷江的历史不可回避地与“沅有芷”这三个汉字发生了一次芬芳的碰撞并影响至今。现存的说法是,芷江之得名,源于屈原《九歌·湘夫人》诗句“沅有芷兮澧有兰”。清同治八年《芷江县志》首持此说,从此成为后世学者无人质疑的一个定论。芷江,芷草有香,江风无限,这是一个极富诗意且清香四溢的地名。无人质疑,没有人忍心去质疑,或者根本没必要为此而质疑。 《九歌·湘夫人》原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集体编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芷江县志》卷一载有“附芷江县名考”一段文字: 清同治八年版《芷江县志·山川志》载:“芷溪,源出明山,流入沅水;近溪山中,向产芷草,今或偶得之,邑之名以此。”另据民国30年由舒新城等合编的《辞海》云:“芷江,(一)《楚辞九歌·湘夫人》:沅有茝兮澧有兰,茝亦作芷,世因称(氵无)水曰芷江。(二)今县名,清置。为沅州府治,城濒(氵无)水北岸;(氵无)水,沅水之源也。(氵无)水别称芷江,县名以此。” 由此可见,民国《辞海》第一说沿用清同治八年《芷江县志》成说,没有异义。其第二说认为“(氵无)水别称芷江,县名以此”,则是以水名县。以水为城镇命名,“芷江”而外,还有周边的“安江”和“洪江”两处。翻阅相关史志,安江地名始于北宋熙宁年间(-)所置安江砦,此前地名“峡州”。洪江地名始于北宋熙宁八年()所设洪江铺,此前地名不详。对于安江、洪江两地名称的义涵,史志均无解说。民间对于洪江其名有一种说法:“洪江”二字去掉三点水便是“共工”,洪江之得名与“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有关。《淮南子》:“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但据古籍所记,无论共工的出生地雅砻江(金沙江支流,俗名“若水”,流经青海、四川两省)还是其活动地域帝丘(今河南省辉县一带)都与洪江无所涉及。民间传闻,聊备一说而已。从现见史籍看,安江、洪江两地设立砦铺都是当年章惇“平定峒酋田元猛之乱”的结果,以“安定”之义解释“安江”之“安”,应该言之成理。“洪江”之名似乎也可以作出相近的推测,“洪”有水势“盛大”的意思,若章惇借此喻指朝廷之“洪”福并暗示自身的功劳,也未尝不可能。我们或许可以改换一下思考方向,安江洪江,两地之得名原由或者与芷江是同一理路:北宋设立安江砦和洪江铺,只是设立了一级军政管理机构,其命名却是沿用了旧称。而旧称的本意在于:安江地邻沅水,水面宽阔,水流相对平缓,取“江水安澜”之意而名之。洪江紧邻巫水,水道逼仄,滩陡浪急,取“洪波涌起”之意而名之。这样的推断,也应当合情合理。芷江、安江、洪江三地得名都关系到“水”,若按其得名时间考察,则“三江”之中的安江、洪江虽以水得名,却都因章惇平定田元猛之事而与政治军事相关。唯独芷江得名晚至清乾隆时,并且纯粹因水得名,与政治军事没有什么牵绊。若芷江因水而得名,看上去与屈原诗歌似乎没什么干系。其实不然,即便水名“芷江”,顾名思义乃是“芷之江”,长满蕙兰的一条河流,还是离不了“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诗句,文人附会,未尝不好。 紫姜及芷江鸭 民间还流传芷江得名的另一种说法:“芷江”由“紫姜”演变而来,如同以佐料得名的“紫姜鸭”演变为以地方得名的“芷江鸭”。这一说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只是误会了一段史料,出了张冠李戴的差错。历史上的确有一个“梓姜县”,只是与“紫姜”以及“芷江县”并非同一称谓,也没有什么历史渊源可寻。 《芷江县志·卷三·建置沿革考》载: 代宗大历五年(),改巫州为溆州潭阳郡,领县三:曰龙标,曰郞(注:当作朗)溪,曰潭阳(析龙标置)。改业州为奖州龙溪郡(今有龙溪市镇,属晃州),领县二:曰峨山,曰渭溪(原按:旧《志》领县三,有梓薑县,今考《湖南通志》,并无)。 这里的“梓薑”即“梓姜”,“薑”“姜”两字形异义近。显然,这里提到的“梓薑”属奖州龙溪郡,而同时的潭阳(芷江)则属溆州潭阳郡,两者有较大的空间距离。 《贵州通志》载: 贞观十二年(),置奖州,设梓姜县。 《贵州通志》又载: 蒋州,《龙溪志》本舞州。长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县置。开元十三年(),更名鹤州。开元二十年(),曰业州。大历五年(),又更名。县三,峨山(本夜郎,天宝元年更名)、渭溪(天授二年析夜郎置)、梓姜(本隶充州,天宝三载废为羁縻州,以县来属)。 这段文字更加明白:唐武则天时,将沅州下属的夜郎、渭溪两县从沅州分析出去,另置舞州。其后于开元十三年、开元二十年、大历五年三度更名为鹤州、业州、蒋州。而“梓姜”本来隶属充州,天宝年间充州改为羁縻州,梓姜归属蒋州。据《镇远府志·卷三·前事志》记载,“梓姜”的治所在今天的贵州镇远县。 另外,还有关于“紫姜苗”的三段记载,因“紫姜”与“梓薑”名称音近,顺便录出,以资参证。一段是《乾隆通志》所载: 紫姜苗,在都匀、丹江、清平者,其人轻生好斗。得仇人,辄啖其肉。夫死妻嫁而后葬,曰“丧有主矣”。其在平越、黄平者,颇通汉语,多为善战,间入行伍。更有读书应试者,见之不识其为苗也。 一段为清人李宗昉的《黔记》所载,内容有所异同: 紫姜苗,在黄平、清平、丹江等处者,与独山之九名九姓同类,轻生好斗。遇伊者,辄生啖其肉。有在平越者,多出入行伍,大力善战。及读书应试者,见之不识其为苗也。 另一段为《镇远府志·卷九·土民志》引《黄平州志》文字: 紫姜苗,男女装束与汉人同,而行事则与夭家(注:即夭苗,一名“黑苗”)类。 以上史料足以说明:无论“梓姜”还是“紫姜”,作为地域之名,与“芷江”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关于芷江得名的历史便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两千三百年前,屈原被流放于湘沅间。其中某一个时段,诗人溯沅水而上,入溆浦,至辰阳……一路回望,一路行吟,留下了《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芬芳歌句。于是,在民间,由“芷溪”而“芷江”,古代的“无水”(今名“?水”)便有了一个新鲜的名字,兰芷芬芳的“芷江”。屈原流放两千零二十五年后的清乾隆元年,古沅州升州为府,沅州州城附郭沅州府城,需要一个不同的名字以示区别。于是,沅州的某位才子灵光闪现,想到了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诗句,想到了环流城邑那条民众别称“芷江”的河流。一语既出,众声附议。从此,州城更名“芷江”。这一命名,既符合以山水命名城邑的惯例,又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芷江”其名,雅俗共赏,便自乾隆初年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巧合的是,就在湖南省沅江县境内,也有一条叫“芷江”的河流。《湖南通志卷二十三·地理志二十三·山川十一》“常德府沅江县”条引《大清一统志》: 芷江,在县西南。湘水分派逆行数十里,北会沅水入洞庭。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两条“芷江”,一条在沅州府,一条在常德府,江头江尾,相距并非遥远。以“芷”名“江”,其得名或许同样与屈原诗歌有关。随手写出,以资旁证可也。 下期请看第三讲 从无阳到芷江 文:曾岸 制作:王刚 编审:田骅周汶 芷江旅游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ulimaosi.com/plmsjc/11055.html
- 上一篇文章: 耳部湿疹,一般由过敏引起,治疗过程中会出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