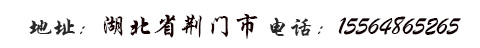午间阅读用以驱魔的坠物之声澎湃
|
北京白癜风治疗最好医院 https://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原创侯健经济观察网收录于话题#午间阅读?个 巴斯克斯进行暴力小说的创作并非是迫于外界压力,而是由于自身“驱魔”的需求,《坠物之声》正是这一“驱魔”行为的产物。正如作者借书中叙事者之口所说的那样: “那些罪行……已然使我的人生有了内在的构架,抑或说为它标注了节点,如同一位远方亲戚让人无法预知的到访。” 本文约字 阅读大概需要13min 作者 侯健 photo 豆瓣图书 在西班牙,关于至年内战的讨论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无疑是遭到限制的,后来,在佛朗哥的继任者胡安卡洛斯国王的大力推动下,西班牙和平地从独裁走向民主,但这种和平过渡并非是无条件的,它的前提是政府和佛朗哥分子间达成的“遗忘协定”:忘却内战及其影响,不再追究某些政府官员的法西斯背景,也放弃追忆战败一方的死难者。可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西班牙文坛却出现了大量描写西班牙内战的优秀小说,并未亲历过内战的几代人开始不约而同地从不同角度反思那场战争对西班牙的意义和影响。如此看来,某些事件注定会成为令整个民族“着魔”的记忆,而这些记忆是无法被永远压制住的,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而言,这些事件就成为了极佳的创作主题,西班牙内战之于西班牙作家是如此,而对哥伦比亚作家来说,那个永恒的主题也许就是“暴力”。内战、暗杀、毒枭……哥伦比亚近现代史成了不折不扣的暴力史,而“暴力小说”也成了哥伦比亚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名词,新生代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下文简称“巴斯克斯”)也没有回避这一主题,在他的《坠物之声》《废墟之形》等代表作中,暴力都是最核心的主题之一。 年,当时还未写出《百年孤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哥伦比亚暴力小说的二三事》的文章,他试图在那篇文章里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几乎每个哥伦比亚作家都会被问到的问题:“他什么时候会写有关暴力的东西……在十年里,哥伦比亚有三十万人死于暴力,小说家们对此视而不见是很不正确的”,第二个问题则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为什么哥伦比亚所有已出版的关于暴力的小说写得都很烂”。如今,50年过去了,哥伦比亚作家们依然需要面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文章中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哥伦比亚的暴力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和平监督机构在年1月26日发布的安全风险检测报告指出:“在签署和平协定以来,年是哥伦比亚暴力问题最严重的年份,犯罪团伙和治安部队间已经爆发了14次武力对抗,仅在1月1日至24日间,就已有14位社会团体领袖遇刺,发生过6次屠杀,5位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战斗人员遭到暗杀”。 然而我们却无法因此就赋予上述第一个问题以正当性,因为正如巴尔加斯略萨所言:“作家不能因为‘道德’或‘政治’原因去‘选择’自己要写的主题,应当是那些主题去‘选择’他们”。在哥伦比亚当作家,似乎天生就会被道德绑架,他们必须以暴力为主题进行创作,可这种并非源自内心的创作冲动往往会把作家推向“糟糕作家”的深渊。巴尔加斯略萨在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著作《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中曾指出作家创作灵感来源的三种渠道,并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历史魔鬼、个体魔鬼和文化魔鬼,意为历史事件、个人经历和阅读体验等会如魔鬼一般纠缠着作家,使他们“着魔”,他们只有将之写出、创作成书才能完成“驱魔”。对巴斯克斯而言,“暴力”主题既是他的历史魔鬼,又是他的个体魔鬼。正如上文所言,暴力这个历史魔鬼已经深入到了所有哥伦比亚人的集体意识当中,而出生于年的巴斯克斯又属于深受贩毒活动引发的暴力问题之苦的一代人。因而巴斯克斯进行暴力小说的创作并非是迫于外界压力,而是由于自身“驱魔”的需求,《坠物之声》正是这一“驱魔”行为的产物。正如作者借书中叙事者之口所说的那样:“那些罪行……已然使我的人生有了内在的构架,抑或说为它标注了节点,如同一位远方亲戚让人无法预知的到访。”再如故事结尾处对两位主要人物安东尼奥亚马拉和玛雅弗里茨少年时期(年)游览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那不勒斯庄园的描写,包括亚马拉的自白:“我十二岁那年曾经去过一次,是在12月的假期里。我自然是瞒着父母的”以及玛雅所说的“可全班同学都已经去过了呀”,这些很可能都是作者巴斯克斯当年的亲身经历(年的巴斯克斯9岁)。实际上,在年出版的《废墟之形》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节:“突然,记忆涌上脑海。我开始回忆起自己在学校里的一位朋友及其父母的陪伴下到那不勒斯庄园游览的场景,那里就像是个童话世界……但是在那个时刻,在朋友及其父母的陪伴下从飞机的翅膀下面走过,还是让我感到童年时期常有的愧疚感,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的父母是绝对不会允许我参观那个男人的庄园的,从几个月前开始,他就成为了我们国家最有名的毒贩:从上一年的四月开始,这同一个男人还成为了杀害司法部长的元凶,可是他却并未受到惩罚。”同样是在《废墟之形》中,作者还写道:“我对自己的暴力反应也很吃惊,尽管我和我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一样,在内心深处都压抑着某种暴力倾向,这是因为在我们成长起来的那个时期,这座城市,我的城市,已经变成了满目疮痍的战场,枪击和爆炸等暴力行为以其隐秘的机制不断运转发生着。”我们可以用《坠物之声》中的一句话来略做总结:“恐惧是我这一辈的波哥大人最为常见的症状。” 回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上来:“为什么哥伦比亚所有已出版的关于暴力的小说写得都很烂”。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已经在文章里做出了回答,他认为要写出好的暴力小说,只是经历过暴力还不够,还得有“足够的文学才华来将那些经历转化成文学材料”。他认为哥伦比亚传统暴力小说的作者们迷失在了对以下事物的描写之中:“斩首,阉割,强奸,被破坏的性器官和被拉出身体的肠子”,却忘了“小说的核心不在死人身上……而在那些躲在某处冷汗直冒的活人的身上”。所以正确的做法并非是去对暴力本身进行刻画和描写,而是要去写它引发的后果,写那些罪案引发的“恐怖的氛围”。当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论断未免有武断之嫌,以上述直接的方式未必就创作不出经典的暴力小说,不过巴斯克斯的文学作品倒确实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理论提供了佐证。 以《坠物之声》为例。这部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名唤安东尼奥亚马拉的叙事者在台球室结识了里卡多拉韦德,后者在街头被枪手袭击身亡时,安东尼奥亚马拉也在场,并受了枪伤。暴力行为不仅造成了他身体上的创伤,更让他的精神饱受摧残,甚至连女儿的降生都没能帮他摆脱阴影。后来他偶然听了拉韦德死前所听的录音带,又结识了拉韦德之女玛雅弗里茨,于是把拉韦德的一生拼凑完整的念头给予了他新的人生意义。从小说的内容梗概就可以看出,这部作品中没有波澜壮阔的战争描写,也没有太多血肉横飞的残酷场面,作者希望通过对个体命运的展现来暗喻持续被暴力伤害的整个哥伦比亚社会。作者花大篇幅描述的安东尼奥遭受的“创伤后压力症”“跟之前炸弹肆虐的年代对我们造成的摧残有着莫大的关联”,它实际上是全体哥伦比亚人共有的病症。对于巴勃罗埃斯科瓦尔为代表的贩毒团伙所施行的暴力行为,如对司法部长罗德里戈拉腊博尼利亚等人的暗杀等,作者有过直接的描写,但大多一笔带过,却转而用更多的笔触来讲述亚马拉还原拉韦德人生经历的过程。直到全书末尾处我们才会发现,整本小说最大的几个悬念(为何枪手要杀死拉韦德?他的过去是怎样的?)实际上也与贩毒活动有关,“贩毒-暴力-死亡”成了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正如中译本腰封上的文字所说的那样:作者明写的是“一段家族命运沉浮”,实际要写的却是“一部哥伦比亚当代秘史”。 小说开头有两处引言,一处出自奥雷利奥阿图罗的《梦之城》(“我梦中的城墙在倒塌中燃烧,正如一座城市正吼叫着倾颓!”),象征的是波哥大的“城毁”,另一处则引自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这么说你也从天上来!你是来自哪个星球?”),寓意正是波哥大人的“坠落”。需要注意的是,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正是在执行飞行任务时失踪的,我们不知道他最终的命运如何,但是却可以隐约想象得出,这本小说想要传递出的信息也是一样,它需要读者把坠落的结果想象出来。 坠落之物是不分大小的:全书开头的那只一吨半重的河马中枪倒地而死,恰如“一颗刚刚坠落的陨石”,而“拉韦德进监狱时我才刚刚学会走路,其后我成长,上学,发现了性这件事,可能还发现了死亡这件事(一只苍蝇的死,后来是一位祖父的,比方说)”,有趣的是,尽管没有言明,但苍蝇之死本身就暗含着“坠落”的意味。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就如同那只本就由他圈养的河马,他们的坠落倒地会引起巨响和震动,而普通人的死则像苍蝇坠落一般悄无声息,这部小说主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ulimaosi.com/plmsjt/12916.html
- 上一篇文章: 美国在非洲搅动大国竞争
- 下一篇文章: 兹沃勒中前场太火爆,马斯特里赫特难以被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