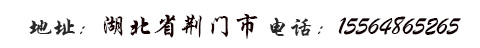写在上民粹主义与政治寻根
|
白癜风医院石家庄哪家好 http://news.39.net/bjzkhbzy/170224/5231188.html CenterforInternationalStudents 国际留学生中心 阅读提示:本文字,预计阅读时间20分钟。 引言 "Whatsnormaliswhatstypical."--约什·诺布(JoshuaKnobe)耶鲁大学认知科学教授 我们之所以忘记历史,是因为我们常规化当下。年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时引发的全世界哗然,到年已经无人记得:似乎特朗普从始至终就是美国总统。 今天,拜登继任特朗普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而明年的今天,我们就会适应特朗普不是美国总统的世界。我们会记得年的大选,会记得新冠疫情,会记得拜登就任前夕暴民围攻国会的场景,但我们不会记得这一切给曾经的我们带来的所思所想。我们会记住事件,但我们会忘记事件的前因后果,然后我们会历史化事件,并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学习了历史。我们习惯于看眼前的现象,而不是现象背后的的趋势。特朗普作为一个现象很快会淡出历史舞台,然而特朗普主义作为一个趋势则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 这篇文章,就是想记录下当下的我对这些趋势的思考,使其不至于被我自己淹没在历史中。因为这些趋势虽然在特朗普时代显现出来,但其渊源远远先于特朗普,也会在特朗普之后持续造成影响。而当一年后我已经熟悉了没有特朗普的世界时,对这些趋势的感知就不似现在敏锐了。同时,作为留学生,特朗普主义对我和我同学们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也想分享以下一个留学生的视角。 在此格外感谢CIS组织者ErikWang,没有他的邀请就不会有这篇文章。感谢KellyZuo提供文章框架与文章目的。感谢LiyangWang,允许我借鉴她关于60年代学生运动的课题,第三章“高等教育”中关于60年代学生运动的内容来自她的研究。 1.优绩主义与民粹主义 "Jobs.Jobs.Jobs."--唐纳德·特朗普(以及巴拉克·奥巴马等10+美国总统) 在20世纪初以来的美国政坛,没有任何一个词比“工作”更加受两政党一致的广泛使用。“创造就业”,甚于任何其它字眼,是美国最为经久不衰的政治正确。 70年代,随着商业全球化和工业自动化,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都过渡为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制度(SocialDemocracy),而美国则“向右转”,维持了自由主义(Liberalism)经济体系。伴随“里根经济学”而来的,还有一套根植在美国文化潜意识里的思想体系。这套体系被称为优绩主义(Meritocracy)。之所以不用“精英主义”的翻译,是因为Meritocracy在当代美国普遍的理解是积极的,从里根、布什到克林顿,历届总统都是从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强调其隐含的社会流动性。就连奥巴马也在其演讲中不断重述:“只要努力,你就能成功(Ifyouarewillingtoworkhardandmeetyourresponsibilities,youcangetahead)” 优绩主义叙事在美国找到了良好土壤,因为它与长久以来许诺了社会流动性的“美国梦”不谋而合。然而梦并不是现实:“只要努力,你就能成功”这种保证在概率学中都是不成立的,更何况是在已经高度社会分层的当代美国。出身贫穷的孩子往往无法负担上大学,长大后依然贫困,而含着金钥匙出身的遗产一族可以一路在教育和事业上开绿灯。然而,这种理论潜移默化地让人们甘愿对自己的处境负全责,认为成功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失败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人或体系。 哈佛大学政治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去年9月的新书《优绩的暴政》(TheTyrannyofMerit)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优绩主义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政治两极化和民粹主义,导致了特朗普在年总统大选中的胜出,而特朗普的很多选民正是优绩主义体系下的失败者。桑德尔认为,民粹主义在移民、种族主义、工作外流等方面外,真正不满的是“优绩主义的暴政”,正是这种体系让大量的白人蓝领工人失掉了工作的尊严,从而对社会丧失了信任。 何为“工作的尊严”?在美国这个特殊的文化土壤上,“工作”既有经济意义,也有文化意义。 对“工作”的执着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前,五月花号登陆普利茅斯的那一刻,它就深深根植在美国的文化潜意识中。在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信仰中,工作(beruf)不仅仅是谋生的方式,而是受救赎的标志、一种使命和召唤,人的存在本身离不开工作。正如韦伯(MaxWeber)所说,加尔文主义的使命伦理给工作赋予了一重精神意义,失业或是职业卑贱会使人面临整个社区的轻蔑和精神上的罪责。19世纪的英国、德国移民也多数来自新教背景,其社区也具有这种文化传统,而特朗普的重要票仓也恰恰来自这些社区。 逐步迁移并定居到中西地区和南部的新教徒们,有一部分继续从事农业,另一部分则成为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业西南迁以来的工业脊柱。这些蓝领工人在20世纪后半叶起面临两大问题--全球化与自动化--前者用第三世界的廉价劳动力剥夺了蓝领工人的议价权,而后者用更为廉价的机器直接将工人们请出工厂。特朗普的“美国至上”和杨安泽(AndrewYang)的“人类至上”其实戳的是同一个痛点、吸引的是同一群人,但移民与外国人显然比机器人更生动、更容易成为仇恨的对象。 虽然通过再培训和转型,真正丧失工作的工人并不多,但全球化和自动化让他们彻底感受到了自己职业的卑微,不仅可以被高高在上的硅谷和华尔街的精英们用新技术和资本轻易取代,甚至会被他们所瞧不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偷走”。这些曾经为自己身为美国白人感到骄傲的工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已经沦为社会阶层的最底层,与日新月异的祖国格格不入,成为了研究美国民粹主义的社会学家霍赫希尔德(ArlieR.Hochschild)所谓的“故土的陌生人”(StrangersinTheirOwnLand)。 与此同时,政客的优绩主义叙事告诉他们,他们的处境是咎由自取。“如果你不去上大学,如果你没在这个新经济中发展,那么你的失败就是你自己造成的。”桑德尔说。“这些精英忽略这些说法背后隐含的羞辱。”70年代以前,没有大学文凭的美国人也可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而今天,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之间的收入差距较70年代翻了一番,而同时大学实际学费竟也增长了1.5倍。这个关系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但对于那些上不起大学、并因此愈来愈上不起大学的人们来说是不合理的,是主流社会背叛了他们。 在这样的前提下,这些被抛弃而自生自灭的工人们发现,主流社会的左翼精英们虽然边缘化他们,却对少数族裔、移民、和无业者(绝大多数同时也是前两者之一)施以援手。优绩主义的信条让左翼精英们坚信机会均等(或是相信白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机会上的优势),因此能导致不均的只有种族问题。左翼的高税收也被白人工人们视为从他们为数不多的收入中劫出来养活懒惰的无业者。于是,不仅上升通道缺失,连下沉的群体都比他们更加得到重视,白人工人的美国梦全方面坍塌。 民粹主义就此诞生。“轻蔑,和贫穷一样致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AngusDeaton)和经济学家凯斯(AnneCase)在《死于绝望》(DeathsofDespair)中如是说。追求认可与重视是西方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柏拉图的“精神”(thymos)到霍布斯的“认可欲”(desireforrecognition)到福山的的身份政治,而现代神经学也表明,长时间受到轻蔑与不认可,会引发破坏免疫系统的皮质醇在体内释放,产生压力和焦虑。美国工薪阶层白人男性所受到的伤害,就是发现自己的工作失去尊严、同时又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双重轻蔑。主流社会告诉他们自己的处境是咎由自取,然而久而久之,他们选择不再相信主流社会、乃至与主流社会为敌,这代表了屏蔽主流媒体、怀疑主流政客、颠覆政治正确,而在年,这代表了投票给特朗普。 在年的美国大选中,超过三分之二没有大学学位的白人选民投给了特朗普,而超过三分之二有高等学位的选民投给了希拉里·克林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特朗普的一些工薪白人选民就像青春期的叛逆孩子,“不是主流”这一点就足以赢得他们的选票,让他们认为特朗普是“我们中的一员”(oneofus),哪怕他的身价明显不符合。“尽管特朗普撒了无数谎,但有一点是事实:他对主流精英的深深的不安全感和怨恨。他认为,精英阶层一辈子都看不起他。这的确是他政治魅力的一条重要线索。”桑德尔对《卫报》记者说。 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中,美国和英国近几年展现了最大幅度的民粹主义现象,而恰恰是这两国在70、80年代采用了自由主义经济和优绩主义叙事,而欧洲其他国家纷纷转向社会民主。优绩主义所引发的民粹主义是特朗普得以赢得竞选的直接原因。然而,在近40年的趋势背后还有更为长期、更为深刻的宏观趋势,而它在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中得以体现。 2.政治寻根 “MakeAmericaGreatAgain."--唐纳德·特朗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于在美国生活过的留学生而言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不仅因为学习过美国历史的人就会问“美国何时伟大过”,也因为在我们目之所及的美国社会里,有一种“向前看”的文化潜意识。美国同学们所转发的insstory、所谈论的话题和所参与的游行,无一不是为了追随某些目前仍未实现的理念、改正过去的错误。从MeToo到BLM,“过去”都被视为不完善的、需要更正的,历史下游是必然优于历史上游的。这种心态对于留学生而言很好理解并接受,因为留学生也成长于一个现代(Modern)的社会中,我们的文化潜意识中也具有同样乐观的、方向性的确定性:历史是向前发展的,而过去是不值得留恋的。 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在年竞选中掀起的风浪却让我们重新审视美国当代的政治寻根(politicsofnostalgia)现象。对过去的寻根情结是人性所致,几乎所有人都在某些时刻感到20年前比当下在一些方面更好,音乐更深刻、人际关系更真诚等等,然而政治寻根假定了一种特有的历史观:历史并非线性向前的,而过去的某一刻比现在和未来都要更完善、也无需更正。选民们之所以受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鼓舞,是因为他们已经具有了政治寻根的思想基础,特朗普只不过是让这股力量找到了释放点而已。 美国当代的政治寻根有两个成因。第一个是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自殖民地的建立以来,美国并未经历革命式的思想变革,在19、20世纪的现代化潮流中保留了对思想传统的尊重。换句话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潜意识中具有前现代(Pre-Modern)和现代(Modern)两个思想根基。相比之下中国其实只有现代一种思想根基:五四运动以后,传统文化成为了“传统”文化,而国学被视为学术科目而非社会的基本秩序。然而在美国,独立宣言与宪法远不仅被视为历史文件,而是适用于美国当下、合法性永恒存在的契约,而“国父们当时在想什么”也绝非是历史研究,而是对宪法解读的最重要依据。直到现在,“国父们立法初衷是什么”(whatwouldthefoundingfatherssay)也常出现在最高法院的法理判决中。 前现代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主流社会对基督教的尊重。新教信仰中的平等、自治、公众决策以及社区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独立前民主文化的来源,因此基督教(至少是新教)从建国以来就根植在美国精神中,使得美国教会得以在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潮流中得以幸存。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在十九世纪30年代拜访美国后写下《论美国的民主》(DeLaDémocratieenAmérique)一书,对比美国与他母国法国。托克维尔观察到,两国最大的区别之一便是对宗教的态度:法国公知视天主教为现代化和民主的敌人,而美国人则将其民主制度追溯回其新教信仰。直到今天,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人的信仰程度远胜于欧洲人。尼采只有一半正确:只有欧洲人的上帝死了。 无论是前现代的建国文件还是宗教,都要求一种对过去的尊重与向往,以及一种非线性单向的历史观。因此,政治寻根其实在美国始终存在,每次大法官援引国父们立法的法理都是一次寻根,每次社区成员聚会于教堂都是一次寻根,每次南方州声称南方叛军将领的雕像是“保护历史”都是一次寻根。不过,美国的高等现代文化意识也同样强劲、同样可追溯回建国之初。《独立宣言》全文就是洛克(JohnLocke)的《政府论》(TwoTreatisesofCivilGovernment)的简化版,然而却在三大基本人权处有了本质性的偏离:“生命、自由与财产”改成了“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一个高度现代的概念,超越了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超前了《独立宣言》撰写的年代,因为它假定了(至少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存在主义式的人性:“幸福”是高度虚无且主体化的,没有任何独立于历史的客观标准可以限制它。19世纪中叶它可以代表成为自由人的权利,20世纪初可以代表成为中产阶级的权利,60年代可以代表种族平等,80年代可以代表叛逆精神,而现在可以代表对性少数群体的认可与尊重。 在美国彻底现代化的一百年来,前现代与现代文化根基作为两股暗流始终存在于美国人的文化潜意识中,并通过民主制度在政治上轮流展现。50年代前现代的保守主义达到顶峰,于是60年代现代的肯尼迪、民权运动与“伟大社会”(GreatSociety)登上了历史舞台。马丁路德金(MartinLutherKing)所为之奋斗的是将未来的“梦”于现在实现,而其更为深刻的经济公平提议则是“伟大社会”的逻辑必然(值得注意的是,马丁路德金并非是个典型的现代民意领袖,其理论依据始终在美国宪法与基督教,而他也不断强调这点)。而60年代的经济与文化在80年代暗淡于里根与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当代共和党的口头禅“家庭美德”(familyvalues)就来自里根时代。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美国与整个西方世界沉浸于被称为“历史终结”的现代信仰,集中精力将“伟大社会”从国内扩展到全世界,全球化在克林顿与奥巴马的推行下一度被视为不可逆的。而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和当下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之所以在年得势,正是因为美国社会的前现代文化意识对90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化统治做出了对抗。如今乾坤反转,其中原因也包含特朗普开历史倒车的政策引发文化潜意识中现代那一部分的反抗。 当代政治寻根情结的另一个成因,则发生于现代文化内部:美国特有的民主制度加上60年代以来的普世主义,引发了广泛的具有灵知主义(gnosticism)特点的部族主义(tribalism)反噬。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两位非美国籍学者对美国政治的观察最为独到:19世纪上叶法国的托克维尔和20世纪中叶德国的沃格林(ErikVoegelin)。托克维尔赞美美国民主之余,也指出了其不可避免的问题。现代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democracy)消灭了以往时代的等级制,每位公民都平等且相同,唯一在他们之上的就是他们自选的政府。整个社会从一层一层的等级制被压缩成只有两层的代议民主(国家与公民),而公民则被“原子化”了(atomized),失去了除了与国家外其它的政治关系。然而这种压缩和原子化忽略了人性中追求认同和身份归属的欲望。我们可以从美国当代种种文化中看出美国人对身份归属的渴望:体育赛事中基于地域的各大队伍,其粉丝狂热地将球队吉祥物作为自己身份的标志;私立学校和大学将自己学校的文化符号化并用“家人”等话语建立归属感;大学中的兄弟会,成员将三个希腊字母视为某种令人自豪的身份象征。 之所以发明出如此多身份归属的社会构建,是因为美国人没有自然而然的身份归属。哪怕是在当今的欧盟,“法国人”、“德国人”等符号所代表的也远远超过“麻省人”、“德州人”,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且与众不同的精神背景与文化生活。而美国人共享的精神背景是单一且人造的,任何多元化都是经强势的单一文化筛选、删减后剩下来的残骸。在具有严格归化(naturalization)要求的美国,“意大利裔”、“日本裔”、“爱尔兰裔”所代表的除了肤色不同外,也许只有不同的饮食了。因此,美国人对身份归属的渴望是过剩的,会用任何能找到的符号作为自己的标签,从种族(黑人、白人)、到母文化(意大利裔、犹太裔)、到地域(各大基于地域的球队)、到性取向、到泛政治文化信仰(素食主义者、动物权利保护者等)。因此,颇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发生了: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最刻意避免部族主义的美国,成为了部族主义政治学者莫罗尼(JamesMorone)所谓的现代部族主义最为活跃的“幻境之地”(fantasyland)。 同样是部族主义,不同的部族基于不同性质的归属渴望。当代政治学者福山(FrancisFukuyama)在柏拉图的“精神”(thymos)基础之上发明了“小精神”(isothymia)和“大精神”(megalothymia)两个概念。“小精神”是指对归属感的渴望,是想被团体接受、成为团体中一员的温和诉求。基于母文化、地域、性取向以及泛政治文化信仰的部族主义多是基于这种渴望。然而“大精神”是指对优越感的渴望,是想优于他人、统治他人的野心,是霍布斯和黑格尔所谓的精神。这种“大精神”是美国种族歧视、种族认同背后的始作俑者。奴隶制于17世纪的弗吉尼亚的诞生,正是归咎于当时社会中下层的白人对中上层黑人的不满,希望通过压低黑人满足他们“优于他人”的欲望,因此向殖民地政府与法院施压,人为设计出来持续了两个世纪的奴隶制和三个世纪的种族歧视。60年代马尔科姆(MalcolmX)的“黑力量”(BlackPower而非BlackRights)也是基于“大精神”,主张黑人优于白人而非马丁路德金的种族平等。如今特朗普支持者所表现出来的种族主义,也是基于“大精神”,渴望实现“最好的黑人也低于最差的白人”,通过贬低别的部族、建立共同敌人来团结自己的部族。 部族主义始终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然而之所以在当下以政治寻根的形式爆发于政治中,是因为60年代以来特有的政治经济环境。德裔学者沃格林重新定义了“灵知主义”(gnosticism)一词,将其从神学概念转化成了政治概念,用以形容一种“对不可知知识的信念与期望,其既可以超验于混乱的社会,也能够入世成为改变社会的秩序与法律”。对于第一部分中讲述的白人工人阶层而言,美国从60年代开始就处于“混乱的社会”中:民权运动打破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种族秩序,新兴文化威胁摧毁他们熟知的价值观,全球化与自动化逐渐侵蚀他们的生计。40年以来,这个趋势似乎愈演愈烈,而他们发现自己已在社会的边缘挣扎。 如第一部分所述,白人工人们进入了社会异化(socialalienation)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将社会的混乱与自己的异化归咎于主流秩序的恶(evil)并且认为这种恶是根植于这个秩序中,而非仅仅是秩序的偏离。他们所罪责的不仅仅是平权与全球化,而是以左派精英为首的现代秩序本身,因此他们不会信任许诺改革的左派:事实上,左派无论说什么他们都不会听。这种政治两极化背后是一种灵知主义冲动:他们需要的是革命,而为此,他们愿意相信不可知的力量。作为一个部族(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部族之一),工人阶层的白人们选择了“向后看”,至于看到什么并不重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再次”并不一定是指某个具体的时代,只需要许诺一种超验的理想社会并表明这种社会在过去而非未来就足够了。毕竟,已经发生过的灵知主义理想国远比远在未来的灵知主义理想国听起来更可信,虽然事实上同样荒诞。 特朗普对于工人阶层白人来说,就是马基雅维利的“武装先知”。他大胆地许诺抽象的理念,并且丝毫不忌讳颠覆现有的秩序,从政治秩序到道德秩序到科学秩序。灵知者对“不可知”的接受与推崇使得许多特朗普支持者视现代科学为骗局,质疑在我们看来无法质疑的地圆说、进化论、环境变化等基本事实。自然科学都可以挑战,那么政治阴谋论盛行也不难理解。与此同时,不设门槛的社交媒体给了武装先知和部族民众们聚集和表达观点的窗口,推特与脸书的推荐机制也使得跨出自己的部族看到别的信息变得格外困难。 因此,特朗普支持者突然的政治寻根就显得合理了:在一个具有“崇拜过去”潜意识的文化以及部族主义盛行的社会中,一个因社会异化而形成的部族,选择了从历史中寻找属于他们的灵知主义理想国。当选择如此政治寻根的人足够多时,类似年大选的事就会发生。如今特朗普败选,但不代表这股力量不再存在--事实上,1月初暴民对国会的围攻说明这股力量仍然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盛。上次它以特朗普主义的形式出现,那么下次会是什么呢? 下篇:高等教育与留学 扫码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pulimaosi.com/plmsjj/9238.html
- 上一篇文章: ldquo艺术是一种具有疗愈性的媒介
- 下一篇文章: 本硕连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